在当前的药物研发、生产和监管中,重点毫无疑问是固体的活性成分,通常被制成粉剂或片剂。而液体形式,被看作中间步骤的产物而不是终点,经常被人们忽视。但是固体活性成分要想最终上市,有个无法绕过的门槛——溶解度,溶解度不好就无法被人体很好的吸收。40-70%的药物研发的失败,都是倒在了溶解度不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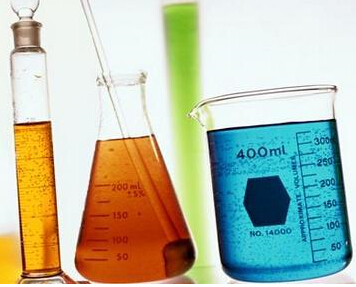
离子液体,作为一类令人激动的可规避上述问题的化合物,却正被人们所忽视。目前市面上销售的药物有一半是由离子键连接在一起的盐。相对于固体形态,在室温或体温状态下为液体的盐具有更好的溶解度、吸收度和稳定性。离子液体还可以一次性递送两种或更多的活性成分。例如,通过将止痛药普鲁卡因的活性离子与非甾体抗炎药(NSAID)水杨酸相结合生成液体盐——普鲁卡因水杨酸盐。它可以更有效、更廉价地发挥这两种化合物的药用功效,同时也开辟了新的治疗方案。
随着现在药物发现的思路越来越停滞不前,是时候尝试替代方案了。我们呼吁化学家和制药业开发药物的液体盐形式。化学家需要更多地了解离子液体的相互作用谱、离子键的设计方法以及离子的选择如何改变离子化合物的化学、物理和生物性质。同时,药物监管机构也需要跟上步伐,把液态活性成分也纳入考虑范围。
为什么离子液体会被忽略?
首先,大多数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化学家缺乏对它们的了解,也缺乏相应的经验。化学课和教科书中告诉我们新分子是通过共价键而非离子键结合在一起的。
其次,制药公司也相对保守,离子液体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不好管理,同时对于商业开发来说也过于冒险。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学术界和产业界的认知问题。在过去20年,许多研究者(包括我们)已经证明了离子液体的巨大价值,可以作为溶剂、电解质和压缩机液,它们可重复使用、不挥发、十分安全。然而,科学家们对这些化合物的绝大多数研究,仍然局限在它们的最初用途上。例如,二烷基咪唑(dialkylimidazolium)、季铵盐和鏻盐(quaternary ammonium and phosphonium salts),还是像20世纪90年代时那样被看作是“绿色”溶剂和电解质。实际上,除了这些“热门”的性质之外,离子液体还有很多很多其它特性。
考虑到液体盐在体内比固体更易溶解,离子液体对生物体产生的作用(如毒性)应该被进一步研究,而不应该被看成是个大问题。
固体的溶解度主要取决于其形态,如颗粒大小、结构是晶体型还是无定型。相同剂量不同形态的效果可能不同,或许无效,或许有毒。这种形态还取决于不可预知的药物生产和储藏条件,如温度、加热和冷却速率以及所用溶剂。上世纪90年代末,抗逆转录病毒利托那韦(ritonavir)被暂时停止生产,这是因为制造的药物胶囊中出现了未曾发现的、溶解度较低的晶体结构,这导致药物的失效。所以,目前的药物开发一般都需要进行固体药物的形态筛选,而对于液体药物来说,这些步骤完全可以砍掉。
离子液体当然不是没有问题,比如它们可能会吸收污染物,会从载体渗出,或者会有目前尚不清楚的生物活性差异。但是在我们看来,离子液体具有提高药物开发、递送和疗效的巨大潜力,足以令研究人员对其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对离子液体的研究
科研人员已经开始研究液体状态下离子键的微妙之处。交换离子可以使盐可溶或不可溶(在给定溶剂中),挥发或不挥发,渗透或不渗透,可反应或不可反应。但还是存在许多未知:如何预测一个给定的离子能否成为液体?如何提纯从未结晶过的活性成分?
离子键的精确差别可进行人为控制。化学家已经研究了质子转移以及氢键对盐熔点的影响,离子穿过细胞膜的难易程度,以及创建不同类型的酸碱复合物。
业界也已经开始注意离子液体。一种基于非甾体抗炎药(NSAID)依托度酸和止痛药利多卡因的离子液体止痛贴,用于治疗背痛,已完成了III期临床试验。对更多离子液体和药物组合的测试是很有必要的,例如,负载于粉末上的离子液体药物可以口服,通过改变粉末载体的性质可以改变药物的溶出速率。
实验室研究表明,药物性质影响其在体内的传递。例如,利多卡因(碱)和布洛芬(酸)的液体组合会在两个组分之间形成强氢键,这会使两种药物同时通过细胞膜。类似的,其它药物的渗透性也能得到增强。在设计固体药用共晶体时,氢键结合的复合物在血液中是结合还是分开,已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



